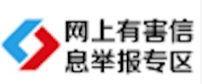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刺下来,将我的影子压缩成脚下一团化不开的墨。我站在空旷的水泥地上,面前的这栋办公楼比印象中矮小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墙体上灰白的涂层被岁月和雨水蚀出了道道蜿蜒的泪痕。我的目光,最终被四楼那个角落的窗口攫住,当年我为防盗而焊接的简易铁架子依旧孤零零地竖立在那里。
风从楼宇缝隙间穿过,拂过铁架,发出极轻微的呜咽。我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正和几位同事围着这新焊好的铁架指指点点,讨论着它的牢靠。那时,我们整个单位也就十来号人。领导的办公室就在三楼转角处,敞着门,谁有事,喊一嗓子便能听见。心是齐的,劲儿是往一处使的。那时候的世界很小,小到一幢楼一片空地,便是安身立命的桃源。
循着记忆里生了锈的楼梯向上,脚步声在空寂的楼道里激起回响,一声又一声,敲打在心跳的节拍上。四楼走廊尽头那扇熟悉的门此刻紧闭,门上贴着白纸黑字“档案库房”。
这是我当年居住过的“套房”。二十多平米,被一道自己用刨花板隔出的墙一分为二。里面是卧室,一张床占去了大半空间;外面是书房兼会客室。那隔断墙曾是我最得意的“工程”。墙面贴满了我从各种报刊上细心裁剪下的投稿联系方式,红蓝铅笔的线条纵横交错,勾勒出采访的提纲与行程。夜深人静时,我就伏在那张老旧的书桌上,就着一盏台灯晕黄的光写下密密麻麻的采访笔记。
而生活的烟火气则在楼下。单位领导体恤,在办公楼右侧的空地上,用石棉瓦和木桩简易搭盖了一排厨房。四位同事一人一小间,七八平方米。但每日黄昏,这里便是整栋楼最生动、最喧腾的所在。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油锅爆响的“刺啦”声,各家菜肴的香气或焦糊气交织缠绕,升腾起一片扎实而暖烘烘的人间滋味。空地旁还有一小块被妻子开垦出的菜地。
下班后,妻子时常挽起袖子,拿起那把被她磨得光亮的锄头在那一小方天地里躬身忙碌。春有青菜夏有瓜,秋有萝卜冬有茄。一年四季,她用双手变换着我家的菜谱。餐桌上那盘清炒时蔬所代表的远不止是果腹,更是一种与泥土悄然达成的默契与和解。
而每日生活里最雷打不动的韵律是接送女儿。从县政府大楼搬来这里时,女儿才上幼儿园,扎着两个翘翘的羊角辫,书包大得快拖到地。从此,清晨与黄昏,我那辆黑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便成了穿梭于家与学校之间最忠实的摆渡船。从幼儿园的一天两趟,到小学、初中,再到高中时因晚自习增加的一天六趟。自行车和摩托车便成了女儿成长路上最恒久的伙伴。她在作文里写道:“爸爸的自行车为了接送我,轮毂都瘦了一圈。”读到这句时,我心头一颤,继而涌起一股混合着辛酸与甜蜜的暖流。孩子用她诗意的眼睛看见了钢铁躯壳下那份沉默的消耗与付出。风里来雨里去,车辙丈量着日升月落,也丈量着一个父亲日益加深的皱纹与女儿日渐抽高的身影。后座上那个小小的重量,我所有奔波最甜蜜的负荷。在这日复一日的迎来送往中,在拥挤却温暖的后座上,家的概念,被具象为一条固定的路线,一份无言的守护。
这间小小的套房盛放了一家三口最稠密的时光,也联接着整栋楼里活泼的生气。女儿很快和同事们的小孩成了朋友。每天作业做完后,孩子们的欢笑声便会从各个角落汇聚起来,在楼道里追逐、回荡。他们玩着最简单的游戏却拥有最丰沛的快乐。那些无忧无虑的喧嚷,是这幢旧楼最动听的心跳。
然而,工作调动的通知还是来了。女儿小学三年级的下半年,我们收拾行囊,告别了这间居住过七年的套房。离别是仓促的,生怕多停留一刻,好不容易积攒的决绝便会溃散。往后这些年,虽也偶尔回上杭,却总像一个近乡情怯的游子,只敢在远处望一眼这片街区的轮廓,从未敢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面去触碰这段被封存的岁月。
“我们回去看看吧。”女儿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唤了起来。她已为人母,身边站着我的小孙女,眼神清澈,正好奇地打量这个妈妈故事里的“古迹”。
套房变成了档案库,寂静无声地呆在原地。而另一个地标却牵引着我们的脚步。距离套房不足二百米的上杭县标志性建筑落成于一九九四年。扬帆起航的造型挺拔地指向天空,前方簇拥着新修的喷水池。每到夜晚彩灯亮起,水柱便随着音乐翩跹,五光十色如梦似幻。那是小城迈向“现代化”最骄傲的宣言,曾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而我的记忆里,关于县标却另有一番滚烫而生动的颜色。县标落成不久,我帮一位乡下亲戚拍照,偶然试了相机的延时拍摄。快门按下,人像清晰,背后县标与喷泉的流光溢彩也一同被定格。那晚,我冲洗出照片效果出奇地好。一个大胆的念头,像喷泉的水花一样冒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许多个夜晚,我肩背一台佳能牌胶片相机,手提简易三角架,在县标璀璨的灯影下当起了一位临时摄影师。我耐心地指导顾客摆姿势,小心地调整角度,然后按下快门,等待那六秒的延时。“咔嚓”一声轻响,对于我和等待的顾客而言,不啻于一次完美的收官。扣除胶卷和冲洗的成本,一张照片能赚一块钱。一个月下来,这笔“外快”竟超过了我的工资。后来,懂这技术的人多了,我便悄然退出。但那一段在华丽县标下用快门捕捉普通人欣悦与憧憬的夜晚,那份粗糙而直接的成就感,至今想起,掌心仍会微微发热。
“当年感觉好远,现在怎么感觉一下子就到了?”女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她正站在当年我曾无数次取景的角度为她的女儿拍照。我环顾四周,是啊,当年那些七拐八拐的旧房屋变成了眼前这片一览无余的停车场。距离被现代化的推土机碾平、拉直,物理的通道便捷了,而心理的回廊却似乎更加幽深曲折。
小孙女在县标基座边跑跑跳跳,女儿的镜头追随着她,脸上是与我当年全然不同却某种情感内核相通的温柔。
我忽然明白。我们重返故地,并非为了寻找旧物。铁架会锈蚀,楼房会易主,县标的喷泉早已不再喷涌。我们寻找的是时光流过时,在心灵河床上冲刷出的痕迹。是当年那个在清贫中认真经营日子、在重复中不懈传递温情的自己。那份“满足安逸”,从来不是物质丰裕的馈赠,而是心灵在专注于当下、创造于当下、去爱于当下时,所自然生发出的、对抗时间荒芜的丰盈力量。
尽管物非人亦非,但当年那般热烈活过、爱过、创造过的证据并未消失。它存在于女儿回望的眼神里,存在于孙女奔跑的笑声中,更存在于我这被往事浸润得沉甸的胸膛里。光阴确实如箭,但有些东西终究带不走。
转身离去时,我没有再回头。因为我知道,那片光影,那缕炊烟,那栋楼,还有那个在灯下贴采访提纲、在夜里按快门的年轻身影,都已经跟我一起装进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