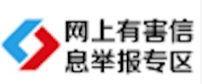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土地承包关系的不变,放活经营权来适应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顺应了农民想保留承包权、又想流转经营权的意愿,既没有回到人民公社归大堆的老路,也没有否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推动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发展,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沿革
中国是消灭了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绝大多数农地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少数农地属于国有农场所有。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即农地的所有权属于村社集体,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分田到户之初土地承包期为15年。按全国对15年不变的理解,这15年主要指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不变,农民具体承包的土地面积和地块还是要变的。因此,在第一轮承包期内,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依据村社集体人口变化而进行的土地调整,“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是普遍现象。土地调整中,村社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也有部分农村,村社集体缺乏进行土地调整的能力,虽然农民有调整土地的诉求,村干部却调不动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种地亏本,以及因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损坏,之前过于细碎的土地难以耕种,农民有强烈的通过土地调整来连片耕种划片承包的诉求,村干部能力比较强的村社集体通过土地调整来满足农民耕作便利的诉求,村干部能力较弱的村社集体因为无力摆平反对派而无法满足农民耕作便利的诉求。
1987年周其仁等在贵州湄潭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改革试点,很快便在全国推广,不久即被修改后的《土地承包法》所吸收。1998年前后全国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正是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很多地方农民认为土地是负担,不愿要承包地,相当部分地区第二轮土地延包走了过场。2001年开始试点农村税费改革,到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土地承包权的利益显现,农村出现了土地承包权的争夺,一些省区进行了完善第二轮土地延包的改革。二轮延包后,土地承包权能更加凸显,2006年《物权法》出台时将农民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用益物权”,村社集体再调整农村土地就变得十分困难。
在全国少数地区比如山东,第二轮土地延包以后,村社集体仍然频繁调整农村土地,调整土地的理由为土地是集体的,集体中每个人都靠土地吃饭,新增人口没有土地没饭吃,去世的人不需要土地吃饭。实际上,土地调整的主要功能不是平均土地权利,或者说,不是公平,而是效率。进入新世纪,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细碎分散的土地不便于耕种,依据农村生产力变化进行土地调整,可以形成便利耕作的土地承包关系,尤其是让农民承包地连片,从而极大地减少劳动投入,提高机械使用效率。因为顺应了农民的需要,有调整土地能力的村社集体成功提高了权威,借土地调整也可以解决村社治理中积存的各种矛盾。山东农村,有土地调整能力的村社集体往往也是治理最好的村社集体。而一些村社集体调整不动土地,也是因为其治理能力太弱,已经无法回应农户对土地公平与效率的诉求,从而造成村社治理能力与土地调整能力的相互弱化。
“三权分置”是释放农业生产力的现实需求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农户进城务工经商,已有1/3的农村土地发生流转,即土地的承包者与经营者发生分离,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土地流转都发生在村社内部,往往是亲朋邻里之间的流转。进城农户一般不倾向将土地长时间一次性地通过正规协议流转给外来工商大户,因为这意味着一旦他们进城失败想再回来种田,就无田可种。反正土地租金有限,不如以较低租金通过口头协议流转给亲朋邻里,租金低但可以随时要回来耕种。
当前农村不仅发生了普遍的农地承包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业老龄化变得普遍,老人农业对于节省体力的农业有强烈需求。同时,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机械化也对土地连片耕种有强烈的需求。分田到户之初,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因此,承包土地时最为强调的是公平,农民承包地因此分得十分细碎,往往一户不足10亩却分在10多处地方。当前经营分散细碎地块,劳动投入太大,而土地连片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效率。因此,全国农村农民出现了普遍且强烈的土地连片承包的诉求,典型如湖北沙洋县的“按户连片”。
越来越多承包土地的农户进城,也就有越来越多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进城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外来工商大户,工商大户要在土地上进行投资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是什么关系,工商大户有多少在土地上进行经营的权利,包括能否以流转来的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的权利。进城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本村亲朋邻里,留村种田的亲朋邻里通过流入土地而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他们从土地上所获收入甚至可能不低于进城务工收入,他们因此就成为村庄内生出来的“中坚农民”。这些“中坚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从进城农户那里流转来的土地分散在各处,一户有50亩适度经营规模,土地却可能有六七十块,分散在全村东南西北不同地方。如果这些土地集中到一块,“中坚农民”种地花费时间将减少一半,农业投入将降低1/3以上。问题是,进城农民将土地流转给留村亲朋邻里,是绝对不愿让亲朋邻里随意变更土地位置以及在土地上进行建设的,且他们是随时可能回来要地自种的。
也就是说,在当前大量农民进城,农业机械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以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释放,降低了农业的效率。基于此,中央提出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即将农地上的权利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将之前归村社集体成员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即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三权分置”也有困境,其中最典型的是土地经营权是什么权?是物权还是债权?若是物权,则中国农地上就有了三重物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都是物权。如果是债权,是由承包权所派生出来的权利,则这样专门设置一个权利就显得有点多余。而且当前农地上的收益十分有限,“三权分置”可能使农地制度运作变复杂。农地上有限的农业剩余可能较难支撑起“三权分置”这样的复杂制度安排及其运作。
给予“中坚农民”更“大”土地经营权
我们来讨论农地经营者的情况。当前绝大多数集体土地仍然由承包土地的农户耕种,这些耕种土地的农户家庭,往往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去了,土地由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耕种,从而出现了普遍的老人农业。此外,还有大约1/3的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出去,发生了承包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而且今后土地流转规模只可能扩大,土地承包者与经营者的分离也就只可能更加普遍。
如前所述,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有两个主要的土地经营者,一是外来工商大户,他们通过正规的土地流转协议来获得土地经营权。二是本村的“中坚农民”,他们往往只是通过口头协议来流入进城农民的土地耕种。工商大户一定希望正规长时期流入农民土地经营权,并可以在流入的农村土地上进行建设,即使流出土地农户进城失败也不可以要回土地耕种。而且工商大户流转土地一定要连片。这样一来,工商大户流转土地就必然是高价流转,土地承包费很高。很高的土地承包费和农业收益有限必然造成大规模流转土地工商大户的经营困境。实际上,最近几年,到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商大户,不少都亏损破产跑路。
另外一个主要的流入土地的经营者是本村“中坚农民”,这些“中坚农民”年富力强,但因为不愿或不能进城务工经商(比如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只种自家承包地又无法获取体面收入,他们就倾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城农民因此将承包地流转到这些不愿或不能进城的农户,村庄内的土地流转,口头协议,随时可以要回自种,土地租金不高。留村农户通过这种不正规口头协议流入三、五十亩土地,再加上其他副业收入,他们在农村的收入就可能不低于进城务工经商,他们也因此可以在农村留得下来,成为农村中的“中坚农民”。他们流入土地后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土地往往过于分散,农业生产中要花费极大精力时间和金钱管理经营分散田块。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从方便机械使用角度,分散细碎的土地也会极大地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无论是从外来工商大户还是本地“中坚农民”角度来看,当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能会限制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相对来讲,我们不应当为了保护工商大户的土地经营权而限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因为这样就可能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害,进而导致农民被从土地上排斥出去。如果给“中坚农民”更“大”的土地经营权,则因为“中坚农民”就是本地农民,在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进城的背景下面,“中坚农民”具有极为重要的治理上的含义,因为正是占农民人口很少的“中坚农民”的存在,为当前中国农村提供了有序的强有力结构支持。
如果农民进城之后,土地主要限制在村庄内流转,则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审视“三权分置”的制度设置,即我们可以考虑,农地上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中,承包权主要包括两种权能,一是农户自家耕种时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二是农户不再耕种承包地时的收益权。当农户不再耕种自己的承包地时,农民应当将土地经营权交还村社集体,村社集体按当地平均地租水平支付交还经营权农户的土地收益。如果农户进城失败返乡要求种地,村社集体则应当给予其承包面积相应的土地经营权。
如此一来,村社集体就同时可以占有两种土地权利,即土地所有权和不再种地农户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如此,在村社范围内,进城农民从土地承包权中获得土地租金收益,且可以随时回村要回土地耕种(当然不一定是自己过去那块地),村社集体则对流入进来的土地经营权在村社范围内进行招标,价高者得,进城农民越多,村社集体就可以掌握更多土地的经营权,从而可以对这些土地按耕作便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可以在招标时尽可能做到土地连片,以便于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国有农场的农业经营体制,十分类似以上设计的“三权分置”制度。即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国有农场的职工有承包国有土地进行耕种获利的权利,但如果国有农场职工自己不种地而进城务工去了,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农场,农场再将土地经营权首先在场内招标再向社会招标,由此很快地解决了农场职工非农化所造成的农地利用上的困境,农场的农地使用效率以及农业生产能力也就比普遍实行承包制的农村集体要高。
在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普遍分离情况下,设置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来满足农业生产力释放的需要,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一个大智慧。